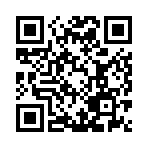青島七旬老人寫百米長(zhǎng)卷 用筆記錄“中國(guó)夢(mèng)”
原標(biāo)題:七旬老人寫百米長(zhǎng)卷 用筆記錄“中國(guó)夢(mèng)”
“分上下兩卷寫,第一卷已經(jīng)寫完,第二卷一百米就差最后的校對(duì)了!”年近七旬的張家榮激動(dòng)地給記者展示他的成果——十九大報(bào)告書法作品,只見卷一已經(jīng)卷成筒狀用麻線捆住,紅色的封皮格外醒目;卷二則半卷著躺在書桌上,上面放著放大鏡和十九大報(bào)告讀本。

張家榮去年做了眼部手術(shù),需要用放大鏡把讀本上的字放大,再謄寫到宣紙上。
張家榮自打退休后,手中的筆就沒放下過,1650米長(zhǎng)的書法版《紅高粱家族》、中英文百米長(zhǎng)卷毛澤東詩(shī)詞、600米十大元帥詩(shī)詞選長(zhǎng)卷……專注于紅色文化創(chuàng)作的他總期待通過自己的努力,給國(guó)家留點(diǎn)東西,給子孫后代留下一些值得保存的記憶。目前,他已寫作近60萬字,明年,他還要寫延安五老的書法作品為建國(guó)70周年獻(xiàn)禮。

創(chuàng)作初期,張家榮沒有經(jīng)驗(yàn),就用不同類型的宣紙和書體來試寫。圖為張家榮書寫的第一卷作品。
初見張家榮時(shí),老人正手握放大鏡,在書房聚精會(huì)神地校對(duì)卷二作品,書房里堆滿了紙,書桌上摞著各種紅色讀本。“當(dāng)時(shí)聽完十九大報(bào)告后,我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動(dòng),腦子里一閃念就決定必須要用自己的筆記錄十九大。”張家榮回憶起當(dāng)時(shí)的場(chǎng)景,情緒激動(dòng),他告訴記者,從那天起,他除了吃飯、鍛煉外,基本都在這里創(chuàng)作,一天最長(zhǎng)能呆11個(gè)多小時(shí)。

張家榮和篆刻達(dá)人李守敬討論如何把書法和篆刻一起融合到作品中。
之所以說“創(chuàng)作”,是因?yàn)閺埨蠣斪硬⒉皇菃渭兊爻瓕懀蔷牟季衷O(shè)計(jì),并把自己的理解融入作品。據(jù)了解,因?yàn)闆]有用書法寫報(bào)告的經(jīng)驗(yàn),他先期試驗(yàn)了半個(gè)月,用了多種書寫格式和字體,才給作品“定調(diào)”。張家榮從書桌旁的一摞紙里一張張?zhí)舫鰜斫o記者展示,說的頭頭是道。“用隸書,長(zhǎng)篇會(huì)讓人產(chǎn)生疲勞感;用草書,能讀懂的人不多;所以最終我選擇楷書、行書結(jié)合,繁體簡(jiǎn)體結(jié)合書寫。在書寫格式上,我開始選擇打紅格,但整體感覺太壓抑,最終確定選擇以白底書寫,顯得大氣磅礴。寬度也得講究,太寬給人以繁瑣的復(fù)雜感,50厘米寬的百米長(zhǎng)卷呈現(xiàn)效果最好!”

張家榮書寫的百米長(zhǎng)卷。
“青年興則國(guó)家興,青年強(qiáng)則國(guó)家強(qiáng)”,記者看到書桌長(zhǎng)卷中“青年”“興”“強(qiáng)”等字的字號(hào)和字體明顯區(qū)別于其他字。“要把總書記的講話精神生動(dòng)地展現(xiàn)出來!” 張老爺子告訴記者,為了打破沉悶的書法,他還對(duì)行文進(jìn)行了藝術(shù)化的處理,諸如“強(qiáng)軍夢(mèng)”“中國(guó)夢(mèng)”等詞語,他都用特殊方法書寫,“比如‘強(qiáng)軍夢(mèng)’,要寫的蒼勁有力,表現(xiàn)出軍隊(duì)的氣魄,戰(zhàn)無不勝的精神。目前我寫過的最大的字長(zhǎng)寬得超過十厘米。”

篆刻達(dá)人李守敬已創(chuàng)作了上千枚獻(xiàn)禮十九大的篆刻作品。
和老人交流中,記者發(fā)現(xiàn),老人的兩眼通紅,每隔幾秒就要眨巴下眼睛。問過之后才知道,他兩眼都患有眼疾,去年7月18日,右眼因黃斑前膜動(dòng)了手術(shù);左眼白內(nèi)障,看東西看不清。“醫(yī)生說最少養(yǎng)半年,但養(yǎng)病期間十九大勝利召開,我必須得寫!” 張家榮的家人都拗不過他,只能在日常提醒老人多注意休息。“其實(shí)還好,看多了,我就用耳朵聽,身臨其境更能體會(huì)到重點(diǎn)。”

李守敬創(chuàng)作的部分篆刻作品展示。
說起這幅長(zhǎng)卷,張家榮有自己的打算,“我和李守敬因書法結(jié)緣,他偏好篆刻,我想請(qǐng)他在書法作品上蓋上他刻的‘中國(guó)夢(mèng)’系列印章,讓這幅作品更有生命力。”據(jù)了解,篆刻達(dá)人李守敬目前已經(jīng)刻了近百枚紅色印章,兩位老人要在上合會(huì)議召開之際,將這幅作品獻(xiàn)出。(記者 余瑞新/文 劉棟/圖)
[編輯:芃芃]- 相關(guān)閱讀 更多 >>
-
- 七旬老人傳承著木版年畫 今年準(zhǔn)備申請(qǐng)"非遺" 2018/02/07
- 七旬老人寒冬走失家屬全城找人 熱心公交人送回家 2018/02/02
- 七旬老人迷失街頭 公交司機(jī)充當(dāng)“引路人” 2017/12/15
- 七旬老人帶600響鞭炮坐火車 最終“忍痛割愛” 2017/12/02
- 七旬老人為占座扒住車門 與乘客起爭(zhēng)執(zhí)動(dòng)了拐杖 2017/11/30
大家愛看
- 1奧特曼演唱會(huì)票價(jià)1280元仍遭瘋搶 情懷消費(fèi)引爆市場(chǎng)
- 2從“丟失焦慮”到“滿電驚喜” 青島地鐵工作人員的暖心守護(hù)
- 3中國(guó)女排留洋軍團(tuán)雙喜臨門 朱婷袁心玥同一天奪冠
- 45人得分上雙 青島男籃客場(chǎng)擊敗浙江廣廈扳平大比分
- 5市民可預(yù)約 北部戰(zhàn)區(qū)海軍4月23日至27日在青島舉行艦艇開放活動(dòng)
- 62025青島馬拉松部分道路臨時(shí)管制 63條公交將調(diào)流
- 7青島地鐵口5平米“神秘土地”無人認(rèn)領(lǐng) 逾期將收歸國(guó)有
- 8螞蟻金服在小紅書上招催收員?官方客服稱將報(bào)警處理
- 9央視曝光假進(jìn)口的保健品 涉事公司多次因食品安全被罰
- 10中國(guó)女冰逆轉(zhuǎn)荷蘭隊(duì) 贏下世錦賽保組關(guān)鍵戰(zhàn)